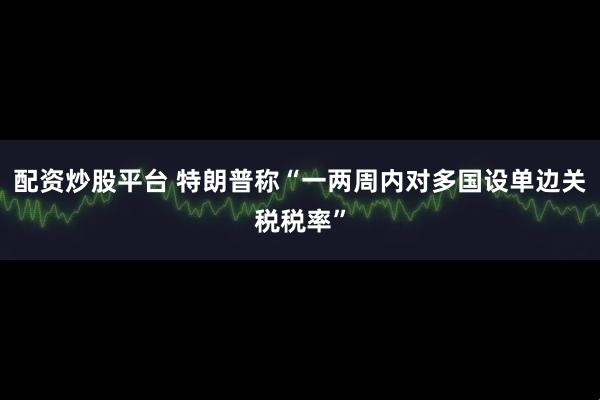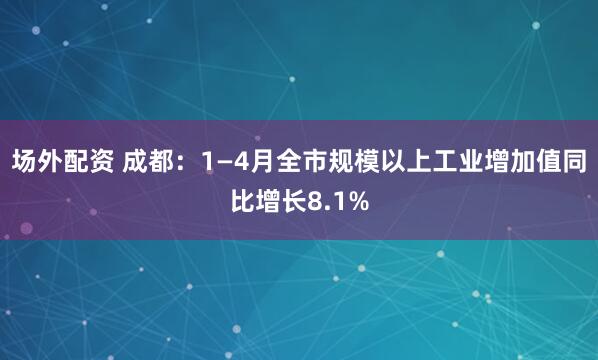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配资之家,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七七事变后,粤港地区先后形成了广州、香港、粤北、东江等战时文化中心。
粤北曲江,这座昔日的边陲小镇,曾经一跃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重要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
这里面,留下了哪些英勇抗战的光辉记忆……
“广东,广东,是我国的边防,是我国的生命线。三千万人齐奋起!奋起!”位于广东韶关的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历史陈列馆里,一本内页泛黄、被翻得卷毛边的《抗战新声》歌谱里,记录了54首抗战歌曲。其中的《保卫大广东》歌词雄壮有力,读起来激昂满腔,让听者仿佛回到80多年前那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
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历史陈列馆中,关于抗战文化活动的展示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多次阐述建立文化军队、开展文化抗日的重要意义。
展开剩余92%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七七事变后,粤港地区先后形成了广州、香港、粤北、东江等战时文化中心。文艺家们在艰苦条件下,以创作观照现实,提振着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为后人留下诸多经典作品。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在韶关走进粤北省委旧址、《新华南》编辑部旧址等红色文化遗存,对话艺术大家、文博馆长,探寻烽火岁月里的文化力量。
黄新波《他并没有死去》
战歌嘹亮
在韶关浈江区五里亭镇良村,一幢外墙泛黄的泥砖瓦平房,原是粤北省委的“红色祖屋”。展柜、展板里展出的《良口烽烟曲》《战地服务队歌》等歌谱,一度回荡在岭南大地的山水间。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迁到粤北。“在广东省委领导和推动下,粤北成为广东新的抗战文化中心。一首首经典抗战歌曲,唱遍中华大地,成为连接亿万同胞的精神纽带。”韶关市博物馆馆长何露说。
1940年夏,第二次粤北会战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一五四师政工队负责人何芷和作曲家黄友棣创作了大合唱《良口烽烟曲》。《良口烽烟曲》一经诞生,颇受粤北群众的欢迎。后来,何芷在《〈良口烽烟曲〉旧忆》一文中写到,该部大合唱是她对战争的实录。
《杜鹃花》词作者芜军(前中),右一为芜军的夫人
同样诞生于粤北后方的,还有抗战名曲《杜鹃花》。早春三月,中山大学哲学系学生方芜军在韶关乐昌坪石村头漫步时,以火海般娇艳的杜鹃花,勾连战士们浴血杀敌的意象,写下新诗《杜鹃花》。黄友棣读后深有感触,仅用一周时间,创作出一首混声四部合唱歌曲《杜鹃花》。
杜鹃花谢了又开,映照战争年代的离合,犹如中国粤北版《喀秋莎》,先在中山大学师生中唱响,后从粤北传遍大江南北。
文化堡垒
中共粤北省委五里亭旧址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城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的唯一环境。”文艺理论家周扬曾提出“战时文化中心转移论”。粤北曲江,这座昔日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重要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便是这一论点的有力例证。
先后转移到曲江地区的文化人有尚仲衣、钟敬文、陈原、梅龚彬、姜君辰、李育中、何家槐、孙慎、麦新、吉联抗、魏中天、张铁生、潘允中等。文化界人士云集曲江,中共广东省委十分重视对曲江抗战文化的领导,成立了以石辟澜为组长的粤北地区党的文化小组,后又成立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
这时的曲江,汇集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粤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广东分会、广东美术学会等文化团体,在大、中学校内也建立了文艺社团。此外,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一队和第七队、第七战区长官编纂部、第七战区政治部政治大队等抗日文化宣传队也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中,进一步促进了曲江抗战文化的发展。
文史学者、党史专家袁小伦在其《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中介绍,成为广东战时文化新据点的曲江,文化人云集,文化活动频繁,文艺作品璀璨似繁星。
这些作品大多刊发于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1939年4月1日,《新华南》在韶关(曲江)创刊,刊物编辑部设于罗沙巷8号一幢小楼的二层,成为当时粤北20多家进步报刊之一。如今,该幢小楼已成为浈江区和平路上的两家商铺,车水马龙,颇有大隐于市之感。
《新华南》创刊号封面刊登黄新波木刻作品《射击手》韶关市博物馆供图
在《新华南》编辑部旧址展厅里,展出了《新华南》创刊号封面——黄新波先生的木刻版画《射击手》。作品通过刻画士兵持枪瞄准的瞬间动态,强化“抵抗”的象征意义,契合战时“以刀为刃”的创作理念。
木刻版画因复制便捷、传播高效,成为重要的抗战宣传媒介。“广东籍艺术家是木刻运动的主力军。抗战爆发后,黄新波、李桦、古元等广东木刻家用艺术凝练起爱国力量。”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林蓝说:“这些版画作品的肌理粗砺,是艺术家深入抗战前线、在子弹横飞的战场上一刀刀刻出来的,在爱国情怀下散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香江文旌
随着时局变化,文化星火南渡香江,一支文化生力军在香港集结起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组织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大批内地知名爱国文化人士经秘密交通线转移至香港。他们先后由上海、武汉、广州、桂林、重庆、昆明等地辗转来到香港。一时间,香港云集了大批中国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先后来港的内地文化人有数百人之多,包括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蔡元培、梁漱溟、欧阳予倩、戴望舒、萧红、萧乾、端木蕻良等等。在内地来港文化力量的推动下,香港成为武汉、广州相继失陷之后的另一文化中心,成为向海外宣传中国抗战的重要窗口。
同时,中共香港党组织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立足长远,力求争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地培养与领导非党员的文化工作干部”,以便更好适应文化人来港工作,使“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致电廖承志,要求在香港建立文化宣传据点,创办报刊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发行。1941年4月,《华商报》创办。此后党组织支持创办或复办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梁漱溟负责的《光明报》等进步出版物。5月初,经中央同意,党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设文学、新闻、学术小组,各小组又分别组织文艺、戏剧、学术、新闻、国际问题和妇女问题座谈会。
在香港文委的领导或组织下,各种文化组织不断涌现,主要有:宋庆龄任名誉会长、颜惠庆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麐、许地山主持的新文学会和世界语协会,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华商报》创刊和中共香港文委的建立,标志着香港文化宣传基地的建立。
《新华南》复刊号
在香港党组织的推动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努力下,战时香港由“文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甚至变成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和“中国的新文化中心”。
东江星火
香港沦陷后,诸多文化力量在东江抗日根据地交汇。这里成为战时粤港地区又一个文化中心。“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后,粤北师生和文艺工作者向东江聚集,实实在在地成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袁小伦说。茅盾、邹韬奋、沈粹缜、胡绳、丁聪等文化人停留东江期间的活动,对根据地文化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使《新百姓报》更有地区特点和代表民意,脱险的文化人建议将该报改名为《东江民报》,邹韬奋亲笔题写了报头,茅盾也为该报的副刊书题“民声”二字。丁聪、特伟两位画家为《东江民报》画了不少漫画。如此多文化名人“加盟”,堪称强大的“明星”办报阵容。
邹韬奋脱险后在东江抗日游击区参观《东江民报》时写给曾生的题词(1942年1月20日)
文化精英与根据地人民、进步青年共同生活,相互学习交融。茅盾在东江谈及对游击生活的感受时说:“这是作家与抗战相结合,创造革命文学的最好机会。”
《东江纵队之歌》曲作者史野则把与音乐家盛家伦的交往,视作其创作的起点。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坦言:“在他们和许许多多从香港回来参加我们部队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我们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有人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州、香港等大城市沦陷以后,广东便没有文艺。其实不然。”正如革命报人黄文俞在《硝烟曲》序言所提醒的:“广东文艺的中心在东江纵队活动的地区,在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希望研究广东文艺史者不要忽略这一点。”
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历史陈列馆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历史档案
抗战时期粤港地区文化活动
粤港地区既是战时中国文化长链条的关键一环,也是中国战时文化中心区之一。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等地大批文化人撤退到粤港地区,与当地文化人汇合。随着时局的变化,粤港地区先后形成了广州、曲江、香港、东江等多个战时文化中心。
武汉、广州沦陷后,大批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和曲江。中共香港党组织重视文化在统一战线和抗战宣传中的作用。其中,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大众生活》《笔谈》《时代文学》等进步出版物远传至东南亚等地,建立起针对海外华侨华人宣传的文化据点。
在粤北,党组织积极领导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占领和开辟了粤北抗战文化阵地,使原本比较落后的粤北山城曲江,随着大批文化人的到来和“文化入伍、文化下乡”运动的展开,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
香港沦陷后,香港文化人进入内地途中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停留,随后多方文化人士在东江抗日根据地汇流。粤港地区文化人以笔为枪,通过文化阵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展现出具体而多彩的粤港战时文化历史图景。
1939年,宋庆龄(中)与漫画家丁聪(左)、陈烟桥(右)在香港的合照
专家点评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
重温文艺经典 体悟伟大抗战精神
羊城晚报·羊城派: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粤北和香港等地文化抗战及其作用?
林蓝: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领导和影响了粤港地区抗战文化事业和反法西斯文化事业,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作出了重要贡献。
艺术前辈们以笔为刀,把舞台视作战场,将抗战热情融入艺术创作中。其中黄新波、胡根天等前辈,他们都曾在粤北工作,以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实践,持守中华民族文化本色,激励全民抗战斗志。
羊城晚报·羊城派:广东美术在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体现岭南画学、广东文化的精神?
林蓝:岭南画学在诞生之初即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在艺术上倡导革新,强调关注现实人生,这在抗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百年前民族危亡之际,高剑父先生创作的《东战场的烈焰》,聚焦一·二八淞沪抗战,描绘了日军炸毁上海闸北东方图书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广州沦陷以后,关山月先生创作长卷《从城市撤退》,这不仅是艺术家个人在广州沦陷以后的逃难经历,更是战时中国沦陷区城市民众苦难的缩影。
广东美术家更在动荡烽火里,守正中华文脉。广东近现代美术教育先驱胡根天先生,在战时辗转韶关曲江等地,在粤北建立起战时艺术馆博物馆,征集战时流落在民间的国家文物,收获了古物数百件,珍贵图书数千册。这些国家文物在战后得以重聚,博物馆也成为战时的“文化后方”。
羊城晚报·羊城派: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广东文艺界将如何回顾历史,为当下带来启示?
林蓝:今年以来,我们正筹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展览”。展览汇聚数百件体现广东文艺工作者以笔当刀投身于抗战事业的原作,全方位展示美术、音乐、摄影、电影、文学、戏剧等多种艺术门类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们在反抗外敌侵略和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卓著贡献。
这些“染着硝烟的艺术”,系统全面地展现广东文艺工作者的抗战历程与成果,它们既是对侵略暴行的无声控诉,更是民族精魂的艺术熔铸。
我们希望和观众一起回顾这段历史,回顾这些创作于烽火当中的艺术经典。从抗战题材经典文艺作品的背后故事中,重温抗战历史,铭记历史警示,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让艺术所见证的苦难,化作守护和平的精神长城。
记者手记
一代文化人的精气神
在马思聪的《我怎样作抗战歌》中,我们读到了一代文化人的精气神。
广州沦陷之际,音乐家马思聪与作家欧阳山联袂创作了粤语歌曲《武装保卫华南》。他说:“轰炸下的广州留在我胸中的不是恐怖,却是激昂……在高压力下提炼出更坚强的战斗精神。”
于民族危亡之际,从云山珠水、狮子山下,到南岭崇山、东江之畔,文化人纷纷走上前线,以笔为枪。
民俗学泰斗钟敬文采写了《抗日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枪笔》《牛背脊》等作品,描绘了一批抗日将领的动人形象;音乐人深入农村、前线、军营,马思聪等音乐名家时有公开演出;知名文艺家吴晓邦、梅耐寒、洪深、熊佛西和何培良在粤北活动,让戏剧得到普及和提高……
在战时省会曲江,先后出现了《北江日报》等9家报纸和《新华南》等7种刊物,出版机构陡然增至34家。1941年曲江有书店43间,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印刷厂30间,超过全省总数的一半。
这些粤港的烽烟往事和故人,组成了抗战文化史里的璀璨群星。还有一群人,在静水深流中,护持中华文化根脉。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后来成为新中国广州博物馆首任馆长的胡根天先生。当日寇在沦陷区大肆掠夺中国文物,胡先生坚持在粤桂后方跋山涉水,搜罗文物,存续文化火种。
最近,《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出版发行。该书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讲述他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的文化抗战故事。
唯有心存希望,才能在极端艰苦的时刻,依然目光长远,步履坚定。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他们护持日常生活中看似“无用”的文化艺术,何尝不是出自对中国必胜的信心!
来源 | 《羊城晚报》2025年8月16日A04版报道
编排 | 刘 佳
编辑 | 梅钰琳
责编 | 谭 明配资之家
发布于:北京市大财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